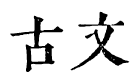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,不覺歡喜,痰迷心竅,昏絕於地。家人、媳婦和丫鬟、娘子都慌了,快請老爺進來。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,連叫母親不應,忙將老太太抬放床上,請了醫生來。醫生說:﹁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,不可治了。﹂連請了幾個醫生,都是如此說,范舉人越發慌了。夫妻兩個,守著哭泣,一面製備後事。挨到黃昏時分,老太太淹淹一息,歸天去了。合家忙了一夜。
次日,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,老太太是犯三七,到期該請僧人追薦。大門上掛了白布球,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。合城紳衿都來弔唁。請了同案的魏好古,穿著衣巾,在前廳陪客。胡老爹上不得臺盤,只好在廚房裏,或女兒房裏,幫著量白布、秤肉,亂竄。
到得二七過了,范舉人念舊,拿了幾兩銀子,交與胡屠戶,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尚做攬頭,請大寺八眾僧人來念經。拜﹁梁皇懺﹂,放焰口,追薦老太太生天。屠戶拿著銀子,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尚家。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著。僧官因有田在左近,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。滕和尚請屠戶坐下,言及:﹁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庵裏,那日貧僧不在家,不曾候得;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,替我做個主人。﹂胡屠戶道:﹁正是,我也多謝他的膏藥。今日不在這裏?﹂滕和尚道:﹁今日不曾來。﹂又問道:﹁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,卻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。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?不見來集上做生意。﹂胡屠戶道:﹁可不是麼?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,合城鄉紳,那一個不到他家來?就是我主顧張老爺、周老爺,在那裏司賓,大長日子,坐著無聊,只拉著我說閒話,陪著喫酒喫飯;見了客來,又要打躬作揖,累個不了。我是個閑散慣了的人,不耐煩作這些事!欲待躲著些,難道是怕小婿怪!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,說道:﹃要至親做甚麼呢?﹄﹂說罷,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。和尚聽了,屁滾尿流,慌忙燒茶,下麵;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眾,並備香、燭、紙馬、寫法等事。胡屠戶喫過麵去。
僧官接了銀子,纔待進城,走不到一里多路,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:﹁慧老爺,為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?﹂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,是佃戶何美之。何美之道:﹁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!因甚事總不來走走?﹂僧官道:﹁不是,我也要來,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,又不肯出價錢,我幾次回斷了他。若到莊上來,他家那佃戶又走過來嘴嘴舌舌,纏個不清。我在寺裏,他有人來尋我,只回他出門去了。﹂何美之道:﹁這也不妨。想不想由他,肯不肯由你。今日無事,且到莊上去坐坐。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,吊在竈上,已經走油了;做的酒,也熟了;不如消繳了他罷。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,怕怎的?﹂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,那腳由不得自己,跟著他走到莊上。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,把火腿切了,酒舀出來盪著。和尚走熱了,坐在天井內,把衣服脫了一件,敞著懷,腆著個肚子,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。
須臾,整理停當,何美之捧出盤子,渾家拎著酒,放在桌子上擺下。和尚上坐,渾家下陪,何美之打橫,把酒來斟。喫著,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。何美之渾家說道:﹁范家老奶奶,我們自小看見他的,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。只有他媳婦兒,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,一雙紅鑲邊的眼睛,一窩子黃頭髮。那日在這裏住,鞋也沒有一雙,夏天靸著個蒲窩子,歪腿爛腳的。而今弄兩件﹁尸皮子﹂穿起來,聽見說做了夫人,好不體面。你說那裏看人去!﹂正喫得興頭,聽得外面敲門甚兇,何美之道:﹁是誰?﹂和尚道:﹁美之,你去看一看。﹂何美之纔開了門,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。看見女人、和尚一桌子坐著,齊說道:﹁好快活!和尚、婦人,大青天白日調情!好僧官老爺!知法犯法!﹂何美之喝道:﹁休胡說!這是我田主人!﹂眾人一頓罵道:﹁田主人!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!﹂不由分說,拿條草繩,把和尚精赤條條,同婦人一繩綑了,將個槓子,穿心抬著;連何美之也帶了。來到南海縣前一個關帝廟前戲臺底下,和尚同婦人拴做一處。候知縣出堂報狀。眾人押著何美之出去,和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。
范舉人因母親佛事,和尚被人拴了,忍耐不得,隨即拿帖子向知縣說了。知縣差班頭將和尚解放,女人著交美之領了家去;一班光棍帶著,明日早堂發落。眾人慌了,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。知縣准了,早堂帶進,罵了幾句,扯一個淡,趕了出去。和尚同眾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。僧官先去范府謝了,次日方帶領僧眾來鋪結壇場,掛佛像,兩邊十殿閻君。喫了開經麵,打動鐃鈸、叮噹,念了一卷經,擺上早齋來。八眾僧人,連司賓的魏相公,共九位,坐了兩席,纔喫著,長班報:﹁有客到!﹂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接進來,便是張、周兩位鄉紳,烏紗帽,淺色員領,粉底皂靴。魏相公陪著一直拱到靈前去了。內中一個和尚向僧官道:﹁方纔進去的,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。他和你是田鄰,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纔是。﹂僧官道:﹁也罷了!張家是甚麼有意思的人!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,那裏是甚麼光棍?就是他的佃戶,商議定了,做鬼做神,來弄送我;不過要簸掉我幾兩銀子,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!使心用心,反害了自身!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,一般也慌了,腆著臉,拿帖子去說,惹的縣主不喜歡!﹂又道:﹁他沒脊骨的事多哩!就像周三房裏,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,是他的外甥女兒。三房裏曾託我說媒,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,好不有錢。張家硬主張著許與方纔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,因他進個學,又說他會作個甚麼詩詞。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薦亡的疏,我拿了給人看,說是倒別了三個字。像這都是作孽!眼見得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,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!﹂說著,聽見靴底響,眾和尚擠擠眼,僧官就不言語了。兩位鄉紳出來,同和尚拱一拱手,魏相公送了出去。眾和尚喫完了齋,洗了臉和手,吹打拜懺,行香放燈,施食散花,跑五方,整整鬧了三晝夜,方纔散了。
光陰彈指,七七之期已過,范舉人出門謝了孝。一日,張靜齋來候問,還有話說。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,穿著衰絰,出來相見,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。張靜齋道:﹁老伯母的大事,我們做子姪的理應效勞。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,也罷了;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。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?可曾定有日期?﹂范舉人道:﹁今年山向不利,只好來秋舉行。但費用尚在不敷。﹂張靜齋屈指一算:﹁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。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,卻是用誰的名?其餘殯儀、桌席、執事、吹打,以及雜用、飯食、破土、謝風水之類,須三百多銀子。﹂正算著,捧出飯來喫了。張靜齋又道:﹁三載居廬,自是正理;但世先生為安葬大事,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,似乎不必拘拘。現今高發之後,並不曾到貴老師處一候。高要地方肥美,或可秋風一二。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,何不相約同行?一路上舟車之費,弟自當措辦,不須世先生費心。﹂范舉人道:﹁極承老先生厚愛,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?﹂張靜齋道:﹁禮有經,亦有權,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。﹂范舉人又謝了。
張靜齋約定日期,雇齊夫馬,帶了從人,取路往高要縣進發。於路上商量說:﹁此來,一者見老師;二來,老太夫人墓誌,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。﹂不一日,進了高要縣。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,二位不好進衙門,只得在一個關帝廟裏坐下,那廟正修大殿,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。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,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著,擺上九個茶盤來。工房坐在下席,執壺斟茶。
喫了一回,外面走進一個人來,方巾闊服,粉底皂靴,蜜蜂眼,高鼻梁,落腮鬍子。那人一進了門,就叫把茶盤子撤了;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,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,那一位是范老先生。二人各自道了姓名。那人道:﹁賤姓嚴,舍下就在咫尺。去歲宗師案臨,倖叨歲薦,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。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?﹂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,嚴貢生不勝欽敬。工房告過失陪,那邊去了。
嚴家家人掇了一個食盒來,又提了一瓶酒,桌上放下,揭開盒蓋,九個盤子,都是雞、鴨、糟魚、火腿之類。嚴貢生請二位老先生上席,斟酒奉過來,說道:﹁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。一來蝸居恐怕褻尊;二來就要進衙門去,恐怕關防有礙。故此備個粗碟,就在此處談談,休嫌輕慢。﹂二位接了酒道:﹁尚未奉謁,倒先取擾。﹂嚴貢生道:﹁不敢,不敢。﹂立著要候乾一杯。二位恐怕臉紅,不敢多用,喫了半杯放下。嚴貢生道:﹁湯父母為人廉靜慈祥,真乃一縣之福。﹂張靜齋道:﹁是;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?﹂嚴貢生道:﹁老先生,人生萬事,都是個緣法,真個勉強不來的。湯父母到任的那日,敝處闔縣紳衿,公搭了一個綵棚,在十里牌迎接。弟站在綵棚門口。須臾,鑼、旗、傘、扇、吹手、夜役,一隊一隊,都過去了。轎子將近,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,一個大鼻梁,方面大耳,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。卻又出奇:幾十人在那裏同接,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只看著小弟一個人。那時有個朋友,同小弟並站著,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,又把眼望一望小弟,悄悄問我:﹁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?﹂小弟從實說:﹁不曾認得。﹂他就癡心,只道父母看的是他,忙搶上幾步,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。不想老父母下了轎,同眾人打躬,倒把眼望了別處,纔曉得從前不是看他,把他羞的要不的。次日,小弟到衙門去謁見,老父母方纔下學回來,諸事忙作一團,卻連忙丟了,叫請小弟進去,換了兩遍茶,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。﹂張鄉紳道:﹁總因你先生為人有品望,所以敝世叔相敬。近來自然時時請教。﹂嚴貢生道:﹁後來倒也不常進去。實不相瞞,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,在鄉里之間,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,所以歷來的父母官,都蒙相愛。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,卻也凡事心照。就如前月縣考,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,叫了進去,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,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,著實關切!﹂范舉人道:﹁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;既然賞鑑令郎,一定是英才可賀。﹂嚴貢生道:﹁豈敢,豈敢。﹂又道:﹁我這高要,是廣東出名縣分。一歲之中,錢糧、耗羨,花、布、牛、驢、漁船、田房稅,不下萬金。﹂又自拿手在桌上畫著,低聲說道:﹁像湯父母這個做法,不過八千金;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,實有萬金。他還有些枝葉,還用著我們幾個要緊的人。﹂說著,恐怕有人聽見,把頭別轉來望著門外。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,望著他道:﹁老爺,家裏請你回去。﹂嚴貢生道:﹁回去做甚麼?﹂小廝道:﹁早上關的那口豬,那人來討了。在家裏吵哩。﹂嚴貢生道:﹁他要豬,拿錢來!﹂小廝道:﹁他說豬是他的。﹂嚴貢生道:﹁我知道了。你先去罷。我就來。﹂那小廝又不肯去。張、范二位道:﹁既然府上有事,老先生竟請回罷。﹂嚴貢生道:﹁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,這口豬原是舍下的……﹂纔說得一句,聽見鑼響,一齊立起身來說道:﹁回衙了。﹂
二位整一整衣帽。叫管家拿著帖子。向貢生謝了擾。一直來到宅門口,投進帖子去。知縣湯奉接了帖子,一個寫﹁世姪張師陸﹂,一個寫﹁門生范進﹂,自心裏沉吟道:﹁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,甚是可厭;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,不好回他。﹂吩咐快請。兩人進來,先是靜齋見過,范進上來敘師生之禮。湯知縣再三謙讓,奉坐喫茶,同靜齋敘了些闊別的話;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,問道:﹁因何不去會試?﹂范進方纔說道:﹁先母見背,遵制丁憂。﹂湯知縣大驚,忙叫換去了吉服,拱進後堂,擺上酒來。席上燕窩、雞、鴨,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、苦瓜,也做兩碗。知縣安了席坐下,用的都是銀鑲杯箸。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,知縣不解其故。靜齋笑道:﹁世先生因尊制,想是不用這個杯箸。﹂知縣忙叫換去,換了一個磁杯,一雙象箸來。范進又不肯舉。靜齋道:﹁這個箸也不用。﹂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,方纔罷了。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,倘或不用葷酒,卻是不曾備辦。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,方纔放心,因說道:﹁卻是得罪的緊。我這敝教,酒席沒有甚麼喫得,只這幾樣小菜,權且用個便飯。敝教只是個牛羊肉,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,所以不敢上席。現今奉旨禁宰耕牛,上司行來牌票甚緊,衙門裏都也莫得喫。﹂掌上燭來,將牌拿出來看著。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,知縣起身向二位道:﹁外邊有個書辦回話,弟去一去就來。﹂
去了一時,只聽得吩咐道:﹁且放在那裏。﹂回來又入席坐下,說了失陪;向張靜齋道:﹁張世兄,你是做過官的,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。就是斷牛肉的話。方纔有幾個教親,共備了五十斤牛肉,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,說是要斷盡了,他們就沒有飯喫,求我略鬆寬些,叫做﹃瞞上不瞞下﹄,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。卻是受得受不得?﹂張靜齋道:﹁老世叔,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。你我做官的人,只知有皇上,那知有教親?想起洪武年間,劉老先生……﹂湯知縣道:﹁那個劉老先生?﹂靜齋道:﹁諱基的了。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,﹃天下有道﹄三句中的第五名。﹂范進插口道:﹁想是第三名?﹂靜齋道:﹁是第五名。那墨卷是弟讀過的。後來入了翰林。洪武私行到他家,就如﹃雪夜訪普﹄的一般。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罎小菜,當面打開看,都是些瓜子金。洪武聖上惱了,說道:﹃他以為天下事都靠著你們書生!﹄到第二日,把劉老先生貶為青田縣知縣,又用毒藥擺死了。這個如何了得!﹂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,又是本朝確切典故,不由得不信;問道:﹁這事如何處置?﹂張靜齋道:﹁依小姪愚見,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。今晚叫他伺候,明日早堂,將這老師夫拿進來,打他幾十個板子,取一面大枷枷了,把牛肉堆在枷上,出一張告示在傍,申明他大膽之處。上司訪知,見世叔一絲不苟,陞遷就在指日。﹂知縣點頭道:﹁十分有理。﹂當下席終,留二位在書房住了。
次日早堂,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雞的積賊。知縣怒道:﹁你這奴才,在我手裏犯過幾次,總不改業!打也不怕,今日如何是好!﹂因取過硃筆來,在他臉上寫了﹁偷雞賊﹂三個字,取一面枷枷了,把他偷的雞,頭向後,尾向前,捆在他頭上,枷了出去。纔出得縣門,那雞屁股裏唰喇的一聲,痾出一拋稀屎來,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,鬍子沾成一片,滴到枷上。兩邊看的人多笑。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,大罵一頓﹁大膽狗奴﹂,重責三十板,取一面大枷,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,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,只剩得兩個眼睛,在縣前示眾。天氣又熱,枷到第二日,牛肉生蛆,第三日,嗚呼死了。
眾回子心裏不伏,一時聚眾數百人,鳴鑼罷市,鬧到縣前來,說道:﹁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,也不該有死罪!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!我們鬧進衙門去,揪他出來,一頓打死,派出一個人來償命!﹂不因這一鬧,有分教:貢生興訟,潛蹤來到省城;鄉紳結親,謁貴竟遊京國。
未知眾回子吵鬧如何,且聽下回分解。